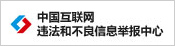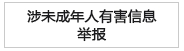《羅峰物語》和五大傳承的匯聚

□ 方堅銘
永強中學甲子校慶,青弘女史為校圖書館造《羅峰物語》大幅甌塑壁畫,丹楓染翠,虬榕披赤,彩舟云淡,星河鷺起,山水清暉,娛人眼目。泉山如籮,龍脊蜿蜒,自括西駛,至海而盡,又適當海之弓,“溫之顯仕巨室,多產茲土”,極見風水之佳勝焉。其作恢弘廣大,微妙清凈,令人觀賞移時,不覺與之俱化。
蓋此非僅一畫也。經此畫之移入,永強中學校園文化品位遂大為提升,乃臻諸五大“傳承”匯聚之妙境,為諸師生熏習陶冶之所。何以故?今茲論之。
世間事若欲成,必待乎因緣。新校區之建成,校慶之舉行,可謂主因也。學校為校慶之事,于建筑設計、校園景觀、慶典主題無不用心,于是禮請偉光兄及不才,拓展慶典主題,乃有“芙蓉花開”之說;禮請青弘為造龍灣山水甌塑,彼乃以行者之清凈心,于畫中融入諸要素,達渾成之境。由是乃有諸傳承匯聚之事。此可謂助緣也。
科舉文化之傳承由此而顯。芙蓉花開,乃意蘊極深之主題。“欲與碧桃爭發達,超然不肯待秋風”,其詩寄物言志,俊逸爽麗。王瓚于弘治八年以芙蓉花早發而兆中舉之瑞,次年以榜眼登科,遂開永嘉場科舉昌大之局。師先賢以自進,期青史以留名,此科第文化,恰可為今日高中生取法。非僅此也,明代四大宗族之文化,由此引入。非僅此也,凡諸龍灣優秀文化,亦由此引入。種種文化之盛宴,奔湊而至,豈可備述之。
實學文化之傳承由此而顯。王瓚、張璁諸人,服膺王儒志、陳傅良之說,持程朱理學力行派,揉和永嘉事功學派,而成實學派之人物,明體達用,修己治人,以經世濟民為己任。無論窮達,均以栽培人才為急,此亦實學之要務也。畫面中有羅峰書院、繚碧園,前者為張璁登科前育才之所,常攜生徒游學河山,溯瑤溪之源,留下川上吟壇之傳說;繚碧園為東嘉雙璧王叔果王叔杲兄弟早年藏游學修之所,靈氣所鐘,景致清幽,別有洞天;王瓚、王激均為大司成,門下弟子甚多,教育理論和實踐豐富,可資強中吸納。
強中若能吸納鄉賢所傳實學精神而為立校之基,必能洗滌污垢,起萎振頹,求真務實,勇猛精進,滋蘭樹蕙,培育英杰無數。
蓮-禪文化之傳承由此而顯。青弘頗好道修禪,尤喜畫蓮。“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漣而不妖,中通外直,不蔓不枝,香遠益清,亭亭凈植,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。”此周茂叔之名篇也,為雅人所愛。佛典中尤重優缽羅華,為禪宗傳心之物。昔日靈鷲峰法會,佛祖手持青蓮,弟子迦葉會心一笑,乃傳其心法,付諸衣缽。青弘于揭幕式上同時發布《迦葉蓮集》,蓋禮敬禪宗初祖之意也。迦葉為天竺初祖,達摩為中土初祖,慧能為壇經六祖,其教外別傳,以心傳心則一也。自唐代以來,禪宗影響中土藝術甚巨。不知禪者,亦不知詩書畫也。藝術之妙,多求韻外之致,味在酸咸之外,與禪家者流通。畫蓮者,欲藉此有相之形式,于無念中,寫此無相之禪意,可謂難也。于泉山溪流中,強中蓮池中,時見此花。不僅為高尚品格之象征,亦為士人心志之所寄。且如張璁之生性好蓮,多植于后花園池中,與其持身特廉、好潔尚直之秉性相合,遂成強中之名花。但有此花在,則藝術之精神在。其香愈遠,則哲學之精微愈顯。菡萏者,實為人類生命之所寄,東方文化之象征體也。
儒釋道文化之傳承由此而顯。由永嘉場士人之儒家立場,及此畫之佛道意蘊,乃知儒釋道文化之傳承,彌布我人之四圍,如蜜入水,侵潤其心。而求其要,無非是修性立命,達至圓成之境。《大學》云:“大學之道,在明明德,在親民,在止于至善。”朱熹《大學章句序》云“人生八歲,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,皆入小學,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,禮樂射御書數之文。及其十有五年……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。”大學之道,即“學為大人君子之學”。高中生學之正其時也,豈僅大學生然。孟子云:“盡心知性知天”,老子云:“玄德深矣遠矣”,佛陀云:“凡所有相,皆是虛妄”。三教之學,奧義無窮,破邪顯正,收拾人心,則一也。青弘又頗好陽明子之學。陽明子于佛道有真經歷,于儒學有真體會,其學通貫三教。于《大學》格致章用力,別成新詮,以“致良知”為了義,以為圣門之“滴骨血”。孟子云“親親而仁民,仁民而愛物”,陽明子亦屢言“萬物一體之仁”,此即安立人天之極則,亦合乎現代生態文明之觀念。我人欲求勝諦,于此能不勉之!
宋明文化之傳承由此而顯。青弘好宋畫,于甌塑中以宋畫流韻行之,別有風味。宋畫為海內外公認之至高藝術,妙合自然,以理趣勝。而永嘉場人士,崛起于明代,于政治文化諸方面多所建樹。今觀此壁畫,合宋明文化元素為一體。學子師法宋明,正其時也。
由此五大傳承之匯聚,乃知今日因緣之殊勝。愿諸強中師生,諦觀思維其義,默會于心,合此五大傳承以造校園之新文化,必能日新其德,光前裕后,再造輝煌。勝士名流,必層出不窮,雖以僻處一隅之庠序,亦隱然有風雷激蕩之氣勢,而為海內外矚目也。
(青弘,原名李昕睿,80后,龍灣人,現在溫州二中擔任“甌塑社團”的導師。本文作者為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教授、文學博士,永強中學87屆校友。)